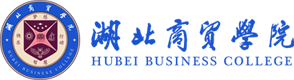延安时期,许多外国友人先后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考察,他们被延安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所吸引感染,通过多种方式向国际社会报道“另一个中国”,向世界呈现一个“热烈的新社会”。“光明”“进步”“文明”“希望”“新世界”等,成为外国友人描绘边区的高频词语。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自力更生的经济形象、安定文明的社会形象,构筑起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善良有效而认真”的治理形象。
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延安时期,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情况是外国友人的重要观测角度。
延安时期,赋予人民广泛、真实、平等的选举权并保障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1937年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继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延安,她在《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对当时的选举权、选举程序、选举比例等进行了详细记叙。按照选举条例规定,除了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犯人外,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包括地主和资本家也有充分的选举权。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认为,“边区的政治是全中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的”,因为“现在一切阶级都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了”。为了保障选举权利能被充分行使,中国共产党还创造出如豆选、画画、燃香烧洞等投票方式,以保障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人民也能行使权利,这让美国记者斯特朗感叹不已,因为“按照美国或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不可能去投票的。为选举而进行的识字测验,在西方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亚洲这样做就将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三三制”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晋察冀边区是最早实行“三三制”原则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深入边区考察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民主实验场”,重现了一个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法国海军中尉乔治·乌尔曼1942年进入边区,他以亲眼所见证实,“政府本着真正的民主精神,遵循三分之一的代表制”。他称赞“三三制”“已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并为未来的大众代表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4年6月,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在参加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联席会议后确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格地遵守着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激动地写道:边区民主“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它“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
每一个访问过边区的西方人,几乎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共产党治理下的边区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典范。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也普遍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积极力量。1943年7月,美国远东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在《远东观察》上发表文章,将共产党中国称为“民主的中国”,国民党中国称为“封建的中国”。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毕森的文章让美国人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充分动员民众的民主政治,使得“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成了政治上的世外桃源”。
自力更生的经济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空前的经济困难,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不但渡过了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而且经济形势得到明显改善。自力更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之一。
1943年,英国物理学家、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与夫人克兰尔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高大的玉蜀黍沿路都是,一群群的骡子装着货物在路上到处可见”,“整个原野里是一片富有的农作物。这里的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富饶的空气”。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也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伦敦《泰晤士报》、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描述道:“这风景好像一幅织锦,织满了紧贴着崇山峻岭的种着小麦、谷子、棉花、玉蜀黍的农田”,说出了“人民的勤劳和决心”。爱泼斯坦写道:曾经“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在南泥湾,记者们亲眼看见“士兵在田里工作,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不仅参观了士兵们在岩壁上开凿出来的窑洞,看见了“久经战阵的兵士在纺纱,织布,缝军服”,还住进了战士们亲手建造的精致平房,就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顾问莫里斯·武道也不得不承认:“‘丰衣足食’的口号和生产运动的成功,随便你跑到哪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来。”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制造出大量的武器弹药,也令外国观察者叹为观止。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苦心研制的石雷印象最为深刻。这种自制的石雷,连日本的金属地雷探测器也探测不到。观察组成员雷蒙德·卢登回到华盛顿报告说,中共领导的部队严重缺乏物资,但“他们会很好地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物资”。外国友人还发现,医药物品的短缺并没有挫伤边区军民抗战的热情,“反而刺激他们完成了临时的创造品和勉强的代替品”,激发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斗志和创造力。中国药草、药物及化学药品被科学的方法试验着以替代西药,破碎的窗玻璃被制成医院显微镜上的玻璃零件,土质的石膏粉贮藏在密封的瓦器中,当地的熟棉被制成了药棉,医用纱布则由医生护士们在古老的木制纺纱机上织成。
就像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在1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几乎是严密的封锁中,因此,自力更生看来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的形象,通过外国友人的报道,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
安定文明的社会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对边区存在的土匪、二流子、烟毒等问题进行治理和革新,取得显著成效。“五无地域”是乔治·乌尔曼对边区社会形象的生动概括,即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无苛捐杂税。他甚至认为还可以加上第六个,无任何麻烦。事实上,几乎每一位到过边区的访问者,都对边区的良好社会风貌赞叹不已。
彻底根除匪患不仅事关边区人民安居乐业,也关系抗战后方的安全与巩固。通过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清匪策略和措施,到1944年初,边区政府已全部肃清土匪,百余年来困扰陕甘人民的匪患彻底解除。美军观察组在第1号报告中就描述了对延安社会治安的初步印象:“在农村,人们听不到任何土匪骚扰或滋扰闹事。”美军观察组还专门就此撰写报告。在解放区后方游历数月之久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解放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整个地区除了无人地带都没有土匪和民团,而这在国民党区域是经常遇到了”。他甚至调侃地说道,“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
改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是边区政府着力解决的另一个社会问题。经过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不懈努力,绝大部分二流子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些甚至还成了劳动模范。1940年11月,加拿大籍传教士斯坦顿·劳滕施拉格在延安逗留了五天。在提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在共产主义地区,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乞丐”,而且“延安也解决了卖淫问题,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在阅读了这份长达十三页的报告后认为,延安是“一个健康、勤劳(据说延安没有乞丐,也没有失业)的社会”。美军观察组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印证了“延安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的说法。
烟毒也是旧社会遗留给边区政府的最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边区政府不仅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还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经过大力整治,鸦片的种植和吸食逐渐被消灭。爱泼斯坦在发往《纽约时报》的通讯中写道:“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都未能发现确定上述指责的任何证据”。他还以自己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向外界郑重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说,“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外国友人对边区文明健康面貌的描述,既是对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有力回击,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成效的高度赞扬。
总之,无论外国记者、军人、传教士,还是国际观察家、外国情报人员,他们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都给予了积极评价。历史的风云际会里,许多外国友人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的“旁观者”。但就像欧文·拉铁摩尔说的那样,他们“只是在进行观察,既不帮忙,也不参与”。正是这种中立的“旁观者”身份和视角,使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更加客观公正、真实可信。选择这些中立旁观的外国友人的记叙进行分析,既能有力佐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也能全面呈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更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为何“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